“当你的女友改名叫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总归是余光中诗人的忧愁。当哼着《阿里郎》跳着《道拉吉》的民族居然又要宣称汉字是他们发明的时候,谁来教他们一首将军令?
近年来,韩国开展了一连串争夺中华文化的举措:论证孔子是韩国人,抢注端午祭为韩国文化遗产,指称汉字是由韩国人发明的。网民强烈质疑韩国“汉字申遗”,称汉字生机勃勃地活着,无须申遗。也有网友作了讥讽式解读:“韩国牛肉为啥贵——牛都吹到天上了。”(12月12日新快报)
对于有备而来的韩国人,网民的义愤虽然在情理之中,但却于事无补。到头来,只会落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尴尬。毕竟,意气之争不能解决问题,这一点,从世人皆知的端午已经“成功”归属为韩国的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
作为“汉江奇迹”的创造者,韩国在经济“攻城”的同时,文化“略地”也在如火如荼地次第展开着。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文化,也从不同的角度蚕食甚至窃取着古老的中华文化,乃至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所谓的文明发源地正名,以努力跳跃式地延长自己的历史存量。
在虚热的“大国战略”意识的烘烤下,韩国居然成了“拥有9200年文明史”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基于这一元命题,和拥有5000(3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比起来,一些看似不合常理的结论俨然就有了逻辑上的可能。
于是,和中国争夺历史的话语权,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韩国有计划的步步为营的文化紧逼中,我们只好无奈地跌到“贴身防守”的境遇。明明是自己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却不得不靠DNA签订来判定最后的归属。最大的憾处还在于,由于我们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常常要吞下“败诉”的苦果。
韩国在此类文化问题经略上“司马昭之心”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其学者化运作的背后常常会躲藏着官方的影子。2005 年,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韩国斥下巨资进行文化推广,在会上宣称孔子曾希望到韩国生活;活字印刷起源于韩国……
反观我们,在和韩国学者的文化视点对垒上,除了凭借爱国主义做武器,那些本该挺身而出的专家学者似乎不约而同地患上了“集体失语症”。 “文化奶妈”是懒于做卫道士的,他们要么在个性化地解读国学经典,要么就是在个性化解读古学经典的路上。毕竟,其间的名利双收岂能是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所能比拟的?而学术“武器”的匮缺,使得舆情成了空有一腔热血的“义和团”,只好抡起板砖,赤膊上阵。
不管事仓颉造字的索隐,还是甲骨文出土的考据。在某些学者的眼中,一度成为垃圾。“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 的钱玄同也好,“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胡适也罢,都曾经对打开中国历史大门的这把“钥匙”表达了自己的鄙弃。假如他们在天有灵,该给韩国人掌声还是嘘声?
想唱就唱,这首“超女”年度主题曲的下一句是唱的漂亮。可是,这些中国文化的粉丝们,拿什么来支持正版,打击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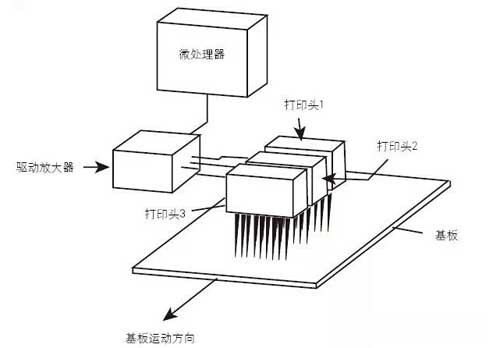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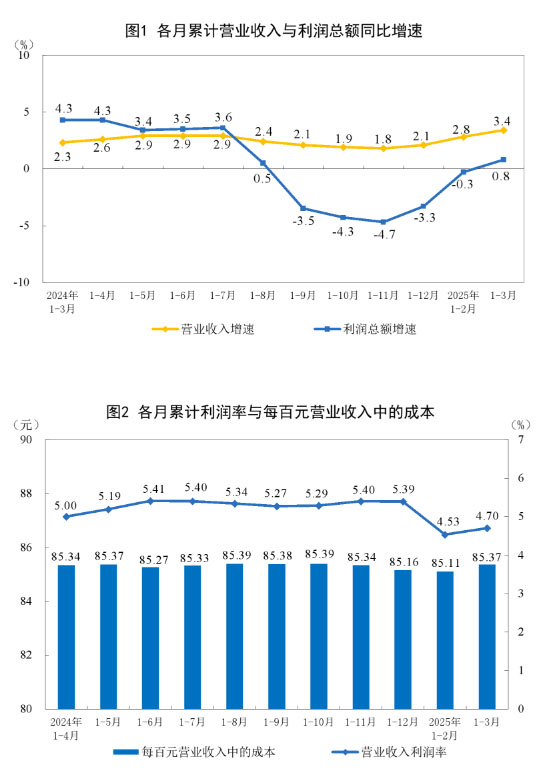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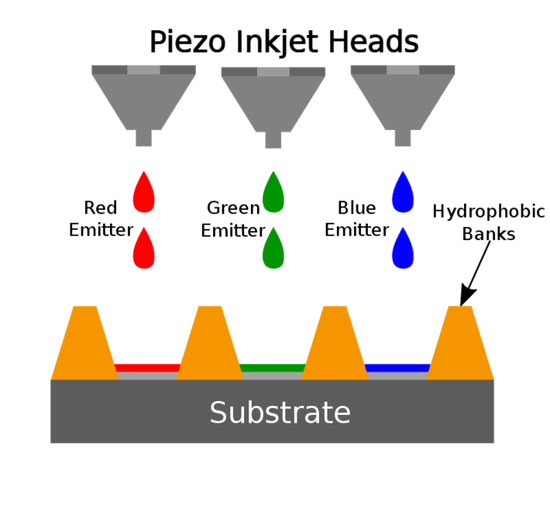
共有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