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从杨柳青年画馆出来,门前是一条无人的小街,前行大约100米,是西青区区级文保单位——安家大院。安家大院对着石家大院后门,与杨柳青年画馆一样,安家大院也鲜有游客。
不过是一宅之隔,繁华与冷清的对比却如此强烈。两条街,两个宅子,两种心情,一如从传统中走来的杨柳青年画,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走进喧闹的时尚世界。
无法替代的师徒传艺
无论是“完全传统派”或是“改良传统派”,霍庆有和张克强都在努力捍卫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时代的躁动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保持这样的清醒和执著。记者在明清街看到,“戴廉增画店”正在营业中,“齐健隆画店”则恰好正在挂招牌。一个老太太推着手推车向游客推销年画,粗糙的画工恰如老太太的介绍“都是自己画的”。在杨柳青,年画带来的经济效益明显打动着每一个人,很多年轻的成功创业者都是通过贩卖年画起家的。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吸引下,民间艺人在挑选徒弟方面更加谨慎小心。
“招收徒弟是个挺费劲的事儿,第一讲悟性灵气,第二讲踏实肯干,两点缺一不可。”霍庆有如今最得意的弟子还是他的儿子,并非有意如此,只是踏实又有悟性的徒弟太难找了。“寒假的时候,我这里来了个‘80后’的男孩,死活非要学习画年画。我看他心诚就留下了,但画了三天,实在不是干这行的料。后来才知道,人家只不过是假期打工,根本就没打算画一辈子年画。”霍庆有的祖辈都是画年画的,民间画师少有大富大贵的,学习画年画只是一种糊口的手艺。“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年画价格越来越高,画师的收入也在增加。很多人学画,不是爱这门艺术,而是看上了画里面的经济效益,这种人是画不出好画的。”
在张克强的画坊里,一个技术成熟的画师月薪高达3000元,但即使这样,仍旧有学成的画师离开画坊自立门户。“在我这儿学徒,试学期间月薪 300,三个月以后适合继续学习的,逐步加薪。每个徒弟我都事先讲好,要踏踏实实能长期工作的,只为学技术的不收。一般情况下,一个悟性高、踏实勤奋的学生,认真学习三到四年,就基本上可以出师了。”张克强认为,杨柳青年画的制作,主要的技艺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的,因此学徒长期的描画实践非常重要。“某大学曾经开设杨柳青年画大专班,我曾经担任主讲教师。但客观地讲,这种两年制的大专班根本无法培养一个技术全面的年画画师,很多技术只是皮毛,学生缺少实践经验,无法实现独立操作。在传授技术上,我还是坚持师徒传艺的方式。”
2009年2月,杨柳青镇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3月,杨柳青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有关报道称,投资1200万元,国内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木版年画博物馆将在杨柳青年画馆原址加以扩建,博物馆建成后的面积将达到3600多平方米。
所有这些都让霍庆有兴奋不已。“政府的力量远远大于民间。有政府直接介入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是杨柳青年画最好的归宿。”霍庆有像是一个熟练的讲解员,说起展室内每一幅木版年画的年代题材仿佛在讲述一个个古老有趣的传说,在他标准的普通话讲解中,杨柳青口音已经很难察觉。而这些,原本不应该是这位杨柳青年画老字号“玉成号”第六代传人的分内之事。但如今,为了向更多的年轻人宣传杨柳青年画,霍庆有不仅把自己的住宅改造成年画工作室和展馆,更亲自参与到画版收藏、资料整理、宣传讲解等工作中。渺小的民间保护力量由于年轻时学过“木匠”,霍庆有是目前杨柳青镇上唯一掌握木版雕刻技术的人。 “按照杨柳青年画传统技法,勾、刻、刷、画、裱缺一不可,其中的‘刻’就是指雕刻画版。现在镇上很多作坊恢复了传统技法生产年画,勾、刷、画、裱四个流程都能够实现,刻版这个步骤,却几乎没有画师可以自己完成。杨柳青年画自明末兴起,至今400余年,明代的刻版濒临绝迹,我个人能够收藏到的最早的刻版不过清代中晚期,所以收集保存内容丰富的年画刻版,是保护杨柳青年画的物质基础。”
在霍庆有的家庭博物馆里,一块乌黑的清代刻版被当作“镇馆之宝”。“这块刻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古玩市场收集回来的,画版长1.4米,宽 0.7米,这种尺寸在杨柳青镇现存的年画刻版当中绝无仅有。”从刻版的画风分析,这块刻版不是杨柳青年画刻版,霍庆有推测应该出自南方某个地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自己能够收藏到这样的“好东西”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几年前,一个韩国收藏家的到访,却勾起了霍庆有心中的一丝遗憾。“他到我家来参观,我便向他介绍自己收藏的这块刻版,还特别强调了它的面积,炫耀说这么大的刻版在国内已经很少见。只见我话音刚落,韩国人嘴角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我心里一惊,难道我说错了什么,让韩国人耻笑了?”原来,这个韩国人也喜欢收藏年画刻版,而就在他韩国的个人博物馆里,也藏有相同大小的一块刻版。
“我对韩国人说,你那块版我见过,为什么我没有收藏呢?因为那块版不够好,是我淘汰不要的。”为了一点点淳朴的自尊心,霍庆有编织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但在内心深处,隐隐的痛从那遥远的年代缓缓袭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天津第二石油化工公司工作的霍庆有带着省吃俭用积攒的几千块钱去“寻宝 ”。在古玩市场,他一眼看中了三块漆黑的木版。“当时一共有三块刻版,都是这么大的面积,三块刻版绘制了不同的内容。我当然是爱不释手,只可惜囊中羞涩,最后挑来挑去花4000元带回来了这一块。我当时叮嘱那个老板,说剩下的两块一定要给我留着,但是等到我凑足了钱再去买的时候,两块刻版都已经卖出去了。 ”在霍庆有心中,多年来一直打着这个心结,没想到其中的一块已经流传到韩国。“我把那块画版的内容描绘了出来,并且指出画版背面还有一个龙首,韩国人听得连连挑起大拇指,我心里面却是哭笑不得。只希望另外一块被国内藏家收藏,无论如何,中国的民间艺术应该留在中国。”
彷徨着传承或是创新在杨柳青镇上,年画的制作如今分为“完全传统派”和“改良传统派”。在是否坚持传统,如何坚持传统的问题上,两个派别虽然没有针锋相对的论战,但却在各自的坚守中执拗地前行。
霍庆有算是“完全传统派”的绝对支持者,在他的家庭作坊里,夫妻、父子、师徒是主要的人际关系。同样,在年画制作上,他也谨遵父辈教导,勾、刻、刷、画、裱一丝不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传统方法进行。“保护传统民间艺术,怎么保护?我觉得首先要保留,把传统方法改了,就不叫传统了,就无法保护了。”因此,霍庆有倾心于“汲古”,不仅收藏各种年代的画版和年画作品,还常常把一些已经失传的传统图样绘制出来,就为了给后人留个参照。“我小时候学画,老人们常讲过去的画师有门手艺叫‘堆金沥粉’,用金箔画画,描过的地方用手摸着会有凸起感。但这种技术早就失传了,别说现在能有人会这门手艺,就是连一幅‘堆金沥粉’的作品我们都见不到了。这就是丢失的传统,我们应该觉得难过。”
技术回归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回归。但在这两个问题面前,霍庆有常常感到无奈。“工具和原料都是问题,现代工业把人们追根溯源的路给堵死了。比如刻版的工具,市场上没有销售的,更没有所谓‘铁匠’来帮忙制作。我只好买了一套刻石头的工具,再自己动手改造成刻木头的工具。再说纸张,质量好的宣纸可遇不可求。去年我花了几千块买的宣纸,刷出版来纸全裂了,打电话到厂家才得知这批纸少了一道工序。颜料也是问题,过去完全是天然颜料,现在都是化学制剂,稍有不慎就会沉淀、变色。还有装颜料的小酒盅,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改良传统派”似乎明显少了这些困惑。“年画张”创始人之一张克强先生属于“改良传统派”的代表,在杨柳青年画的制作过程中,张克强把原先传统工艺中的木刻版创新为丝版,其他工序不变,绘制的杨柳青年画线条更加流畅,画面更显精美。“我是典型的‘学院派’,对画面的美感要求比较高。首先说明,我并不是反对传统工艺,我哥哥年轻的时候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学徒,传统技法烂熟于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为年画制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之所以抛弃木版改用丝版,是因为考虑到木版雕刻过程中受技术影响不能百分百反映原作的线条美感,而改用丝版后就轻而易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张克强的年画作坊里,画师一样在“画墙”,改良了雕版、刷版两道工艺之后,在彩绘这道工艺上,仍然采取了传统的流水线作业方式,画师的一招一式都透出精心。
技术的变革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年画张”的年产量大约在一万张左右,而霍庆有的家庭作坊年产量仅为2000张左右,考虑到人工及熟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用新技术的画坊产量至少比传统手工画坊产量高出一到两倍。
趣说天津话 损 文/林 希 一切的不完整,都视为“损”,财产损失,物质损失,直到精神损失,都可以用“损”字概括。
天津话的“损”,内容比规范语言更丰富。
天津话“损”,指的是道德缺欠,“损”——有损于道德完整,但“损”不同于坏。坏是故意伤害他人,甚至于触犯刑律。坏蛋,坏人,坏分子,要受到法律制裁,“损”,不触犯刑律,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因为太“损”被公安局带走了,还坐牢的。法律再严,治不了“损”,因为“损”对于任何人不构成伤害,不会因为被“损”了一场得了大病,再气死或者投河自杀,“损”就是不够善良,天津人骂人,损德堂,够厉害的了。
马三立先生的相声,《佛心儿》,脖子后边痒,一伸手捏着一只臭虫,“您把它掐死了”。“没有,我佛心儿,旁边有个胖子,我把它放到胖子脖子里边了。”“您太损了。”
这个“损”,能判刑吗?
不算缺德,是损德。
不光是有损于道德的行为是“损”,一切有损于完美的,都是“损”。
出门遇到不吉祥的事,“今天真损”,这个“损”,平声,不开心,做一件事情,不光彩,不嫌“损”,不怕丢脸。
脸子不好看,过去“事难办,话难听,脸难看”,一张“损脸子”,谁看见也堵心。
“损”的发展,“损鸟”,一天到晚不高兴,自闭症,“德性,臭损鸟”,谁也不答理他了。
题材丰富的杨柳青年画(翻拍) 传说 链接 杨柳青年画
三大名号杨柳青的年画业发展,主要得益于清中期专业画坊的兴起,而其中又以戴廉增、齐建隆最为出众。民国时期,玉成号落脚杨柳青,成为继戴、齐两家之后较为知名的民间画坊。
据《杨柳青镇志》记载:戴氏先人自明永乐年间,携画艺从江南随漕船北上,至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到民国时期,戴廉增敬记画店停业,传19代,历时500年。戴廉增是戴氏第九代传人,乾隆中期首创“戴廉增画店”,始在年画左下角加印“戴廉增”字样。自乾隆至光绪,戴氏共建画店19处,成了我国北方画业的巨擘。
齐氏一家迁入较晚,据《杨柳青镇志》记载,康熙年间,齐氏自山东迁来杨柳青,以裱画为业。嘉庆十九年(1815年)兴办“齐健隆画店”,时与“戴廉增画店”齐名。其规模虽稍逊于戴氏,但画艺精堪居首位。
1926年,霍氏第五代传人霍玉堂创建杨柳青镇规模最大的玉成号画庄。但是由于战乱,玉成号画庄不久便衰落下来,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柳青年画行业处于低谷。1950年,霍玉堂联合年画印刷艺人韩春荣,彩绘艺人张兴泽,恢复年画生产。后又吸收年画艺人路恩荣、尹清山、王顺安等办起了画业生产互助组,进而成立“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走上合作发展的道路。合作社即为“天津杨柳青画店”前身。
“娃娃抱鱼”
从何而来?
杨柳青年画在民间最具代表的形象当数“娃娃抱鱼”形象,但这个丰满、喜庆的“大胖小子”究竟从何而来?杨柳青画馆的工作人员和几位民间艺人都说不清楚,只看见清代的刻版上已经是这个模样,民间艺人们也中规中矩将这个形象一代代传递着。
传说清乾隆年间,河北胜芳有个叫薛富贵的穷人,从杨柳青买了一幅《莲年有鱼》带回老家过年。薛家老两口心里高兴,越看画上的胖小子越喜欢。这天夜里,薛富贵做了个梦,梦见画上的胖小子活了,他对薛富贵说:“老爷爷,想吃鱼,我会逮,您快去拿个木盆来。”薛富贵睁眼一看,娃娃还在画上呢,哪有什么捉鱼的事儿啊。
薛富贵把做梦的事儿说给老伴儿听,老太太听罢高兴得直拍大腿。原来,杨柳青年画有个民间说法,叫做“年年鼓”。“鼓”就是“活”,就像“神笔马良”画的画,画中人会从画里走出来,给百姓送福。莫非今天薛富贵也遇上了这等好事儿?他赶忙叫老伴找来一个大木盆,对画上的胖小子说:“你刚才的话我可听真了,木盆在此,我们就等着鱼吃了。”说罢,合眼睡觉,第二天早上,木盆里果真有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
从这天开始,薛富贵老两口天天吃鱼,越来越不满足。他对画上的胖小子说:“一条鱼太少了,每天给我一筐鱼。”胖小子果然每天送来一筐鱼,薛富贵每天卖鱼,日子越过越好。日复一日,薛富贵又不满足了,他掐着指头盘算,要是鱼再多些,过不了多久,这整个胜芳都要姓薛了。他想跟画上的胖小子商量,每天给他十筐鱼好不好,一抬头却看见墙上的画已变成了一张白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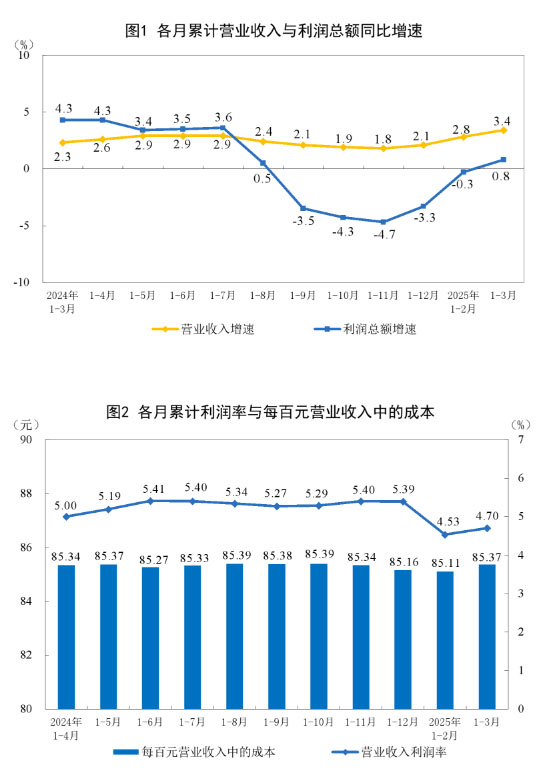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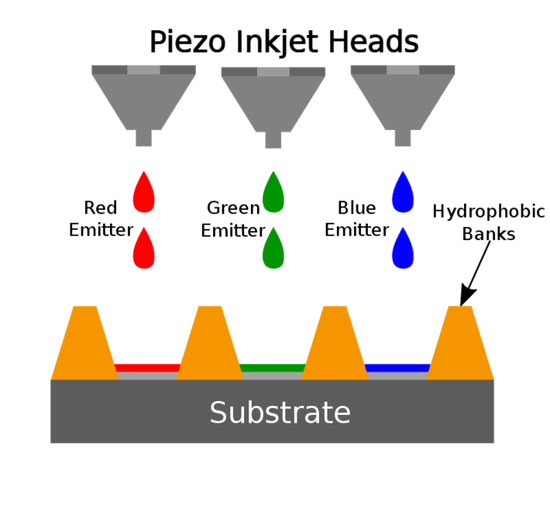

共有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