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凌晨4时,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驶离省科技馆。
车上乘客全部是前往浙江嘉兴观测7月22日日全食的科普夏令营的营员们。
“据说这次日全食是500年一遇,可见这次观测机会的珍贵。”科普夏令营的组织者、省科技馆副馆长陈雪刚说,据预测,下一次在我国境内看到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
“看哈雷彗星给我们那一代人埋下了对天文感兴趣的种子。”天文爱好者张海鹰说,希望7月22日的日全食,为这一代青少年再次埋下科普的种子。
随着7月22日观测时间的临近,笔者在省会采访发现,科技馆、商场、书店、网络……与日全食相关 的方方面面似乎都被卷入一股科普的热潮中。
1.日全食夏令营报名超员
“本来准备组织三十人左右,结果报名人数远远超出我们的预计。”7月20日,坐在行驶在高速公路的大巴上,省科技馆副馆长陈雪刚告诉笔者,他们组织到嘉兴观测日全食的科普夏令营报名异常“火爆”。
就在临出发前两天,还不断有报名电话打到陈雪刚的办公室,尽管报名早已停止了。“去实地亲眼目睹日全食,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长。”1240元的夏令营费用说不上便宜,但依然难以阻挡众多家长为孩子报名的热情。“为了保证观测质量,我们只好控制人数,就是这样还是超了七八个。”陈雪刚笑着透露说,许多人为了参加夏令营甚至走起了“后门”。
其实在去年8月1日赴新疆、甘肃观测日全食后,河北省科技馆就开始运作这次夏令营。但今年初,陈雪刚前往嘉兴“踩点”时,还是发现“下手晚了”。“我们费了好大劲通过当地教育局联系的一家学校,一年前已被日本一家机构提前预定,无法再给我们的观测活动提供接待。”陈雪刚说,一番周折后,他们才最终将这次观测地选定在了嘉兴凤桥镇一所农村小学里。“据说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天文爱好者在嘉兴观测日全食。”
笔者了解到,不仅省科技馆组织的夏令营“火爆”,省会类似夏令营也普遍受到青睐。据石家庄市青少年宫介绍,他们组织的日全食科技体验营也早早招够了赴武汉观测的30多位营员。
2.“星友”自费去“逐日”
“一个普通天文爱好者一生都很难看到一次完整的日全食。”7月20日,省会星空之友俱乐部的“星友”张海鹰、刘和荣和赵永晶同样也赶往嘉兴观测难得的日全食。
虽然此次日全食最长也不过几分钟,可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近一年。早在去年8月1日从新疆观测日全食回来,星空之友俱乐部的发烧友们就开始准备这次“逐日”之旅了。
“看哈雷彗星给我们那一代人埋下了对天文感兴趣的种子。”天文爱好者张海鹰说,他希望7月22日的日全食,为这一代青少年再次埋下科普的种子。
“主要是准备器材和储备知识。”为了能够记录日全食发生的全过程,张海鹰和朋友们一点一点研究拍摄技术。
“日全食发生时,光线是不断变化的,天色逐渐变暗,最后变黑,然后又逐渐变亮。”张海鹰说,“这就需要拍照时不断变换曝光量。”
准备了快一年,如果“老天”不赏脸,来个阴天下雨,那一年的辛苦就全泡汤了。“一片云彩都可能会给观测者带来终生的遗憾。”为此,“追着太阳、躲着云彩”的他们早早就开始关注嘉兴的天气,“万一天气有变化,赶紧换地方。”
有人不理解地问他们:“又不是学生需要普及科普知识,有啥必要花钱跑那么远看一次日全食?”
“很多东西不身临其境是不会理解的。”张海鹰这样解释他们的初衷。
“看着浩瀚的星空才知道人的渺小,你才能静下心来,反观自己的人生。”由于观测天象,赵永晶常生发这样的感慨:“辉煌的太阳和璀璨的星光可以点缀我们平淡无味 的 生活。”
3.科普讲座受青睐
今年河北省科技馆曾组织了两次关于日全食知识的科普讲座,7月初举办的第二次讲座的“上座率”明 显高于第一次。
“第二次培训讲座的票,在十几分钟内就被‘抢’光。讲 座时全场240个座位全部坐满。”省科技馆的刘瑞锋说,近几年这种场面并不多见。
“除了日全食当天实地观测,我们还组织营员们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参观,主要是为了增加营员们天文等方面的科普知识。”谈起科普夏令营为何将第一站安排为参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省科技馆副馆长陈雪刚这样解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而是一次天文之旅、学习之旅。”陈雪刚强调说,围绕日全食观测,他们沿途还将参观佘山天文台、望远镜生产基地、南京青少年科技馆等。
4. 望远镜销售同比翻番
7月16日,笔者走进一家经营天文观测器材的商店,询问观 测日全食专用的观测眼镜的销售情况,店主说:“观测眼镜已经脱销。”售货员告诉笔者,这几天来,每天都能卖出四五十副观测眼镜。
石家庄星空之友光学仪器公司的经理赵占芳告诉笔者,这个月自己公司望远镜的销售量比以往翻了一番。“这次观测日全食,还吸引了很多学生来我这儿借设备。”他说。“7月22日早上,我们将在石家庄东购广场支起6架望远镜,免费让行人观测。”石家庄市青少年宫的殷惠民则介绍说,“这次是精明的商家主动与我们联系的。”
5.旅行社对热潮措手不及
作为省科技馆科普夏令营的合作伙伴,石家庄国际旅行社国内部副经理李欣说,这次夏令营的住宿安排非常难———“问了十几家宾馆,都被定满了。”
她介绍说,长江沿线的大城市,客房早早就被预定了。像浙江嘉兴等观测点,三星级的客房预定已满,条件稍好的二星级双标房,也预定不上。
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北京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冀告诉笔者,国际天文学界有个颇为有趣的现象,称为“日全食经济圈”。
相对于观测地“日食经济”的红红火火,笔者在石家庄走访多家旅行社发现,他们当中推出专门“逐日”旅游线路的却不多。因为与省科技馆的合作,石家庄国际旅行社才专门为赴嘉兴观测夏令营定制了一条旅游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王巧玲告诉笔者:各旅行社对此普遍缺乏重视。同时,类似观测日全食这种旅游产品,需要有相对专业的知识指导以及配套的天文观测设备。“这次公众科普热情的异常高涨,省内旅行社实在是始料未及。”王巧玲遗憾地表示。
记者感言
别让科普潮来得猛去得快
每有重大的科技新闻,都会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掀起一股科普热潮,如哈雷彗星回归时掀起的哈雷彗星观测热,“神五”、“神六”、“神七”发射时掀起的航空航天知识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热潮似乎很难持久,总是迅速退去,可谓“来得猛去得快”。
面对日全食观测在社会公众中掀起的这股天文热潮,许多人在思考:如何使这样的科普热潮持久些?
“不能仅靠新闻和媒体来推动科普。”北京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李冀面对媒体大声疾呼:“对青少年的科普要长期化系统化,要切实将科普知识注入到学校教育中。”
谁能在夜空中指出北极星的确切位置?一个天文学的基本常识,竟然能难倒不少人甚至包括天体物理专业刚招的硕士研究生。是什么让“天”离青少年越来越远?
在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六门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中,天文学是唯一目前没有被列入中小学正式课程的学科,而大学本科阶段开设天文学专业的高校只有北大、北师大等少数几所。应试教育体制下,父母和学校首先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顺利进入大学。一位天文奥林匹克竞赛获奖的中学生感叹,同样是奥赛,天文奥赛就不像其他数理化奥赛那样可以获得高考加分或免试资格,“在很多人眼里中学生学天文是没有用的。”
今年4月,在参加我国国际天文年纪念大会时,与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建生发出了学校教育要重视天文等学科的呼吁。但愿这次日全食引发的,绝不仅仅是一次短暂的逐日热潮。
省会“星空之友”:披星戴月去“看天”
这是一群“看天”、“逐日”的发烧友。
为了观测天象,他们经常身背器材、脚踏自行车赶到人迹罕至的郊外,天刚黑开始观测,黎明前才收兵。
如今谁都说不清“星空之友”——— 这个天文观测发烧友自发组成的“俱乐部”,是由谁提议、什么时候组建的。“是相同的爱好,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俱乐部成员们几乎众口一词。
7月16日,位于省会某商业楼宇19层的一间办公室,迅速变身为一个小型“俱乐部”。
听说“星空之友”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赵占芳要商量赴嘉兴观测日全食的未尽事宜,几位俱乐部成员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事,匆匆赶来。“天象就是我们的集结号!”“星友”刘和荣说。
2006年,为了拍摄到“神六”的踪迹,他们在封龙山静候了两夜。虽然为了这次拍摄准备了半年多,头一天却什么也没拍到,可“星友”们并没有放弃。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我就拉上老张出了门。”赵占芳说,“老张负责拍摄,我则在远处拦车,让司机师傅帮忙关闭车灯。怕车灯一照过来,什么也拍不上。”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神六”终于被他们的相机捕捉到了。
《秋夜银河》是“星友”们合作的典范之作,曾获得第四届全国天文摄像比赛胶片类摄影作品一等奖。
“拍摄时,一个人当支架,一个人拍摄,全靠高度默契的配合才完成了这样高难度的摄影作品。”刘和荣颇为得意地说,“作品连续曝光就达16分钟。”
文/钟时音 樊江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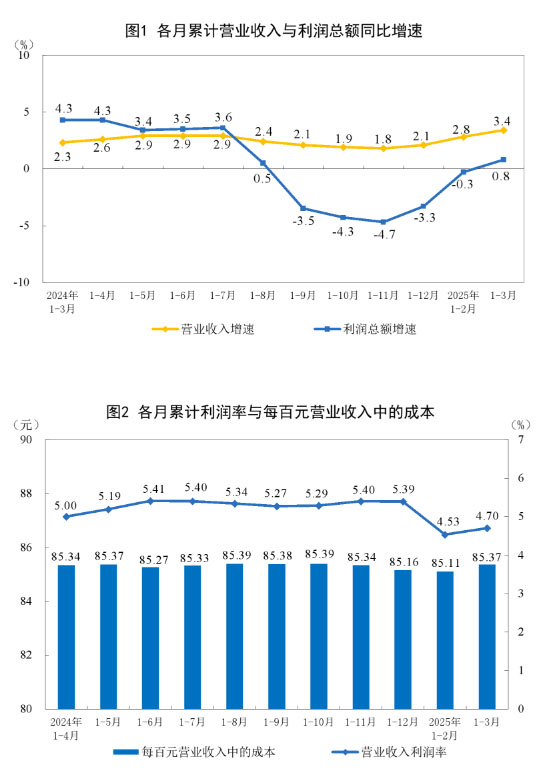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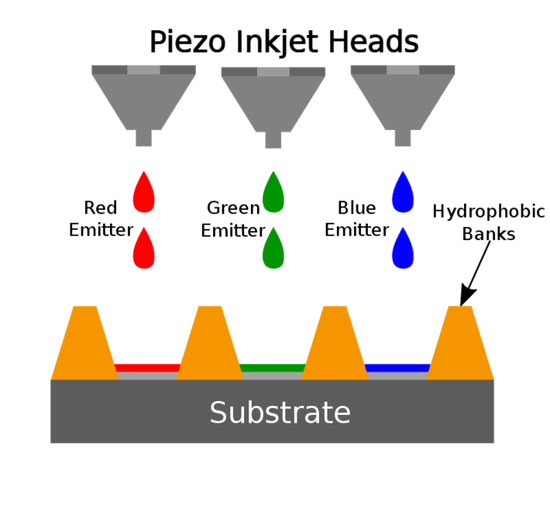

共有 网友评论